
-
第 57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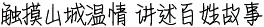
-

第 57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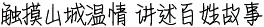


第 57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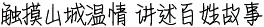

第 57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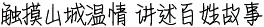







20年笔耕
“一出南津关,两眼泪不干。心想回四川,难上又加难……”91岁的田洪光扯着脖子,唱起川江号子来激昂中带着一丝悲壮,这是一个苦号子,却是田洪光最喜欢的一个号子,因为它反映了当时桡夫的艰辛,正如他花了20年写的书《死了没埋的人》。

旧时的重庆,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挖煤的是“埋了没死的人”,弄船的是“死了没埋的人”。
“重庆是两江汇合的大码头,旧时江上有许多从事跑船、拉纤的桡夫,他们的生活很苦,工作也时常面临危险,但许多人都苦中作乐涌现出不少趣事。”田洪光说,之所以要以桡夫为题材作书,是因为他出身在桡夫家庭,自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

田洪光生在忠县新生区田家坝,那时侯,家里有一条揽载船,父亲靠这条船搭人拉货,养活家里7个孩子。高小毕业后,因为付不起“五斗米的学费”,被迫辍学,12岁时正式成为一名小船夫。每天,在一条“出租车般大小”的木船旁,学习上水拉纤、下水推船,为两岸的人们摆渡。
19岁时,田洪光溯江而上到了重庆,在千厮门做起了桡夫。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入重庆水上公司菜园坝站做一名船工。

每到船靠岸时,田洪光喜欢去码头上找间茶馆,要一碗3分钱的“玻璃茶”,听那些几十年船龄的老师傅摆龙门阵,记下他们口中各个险滩的状况、肉眼看不到的礁石和冬夏风向。有时,老船工们会说起许多江上的传奇故事。田洪光也将这些一并死死地记在脑子里。
“有一回,我和父亲从外婆家回到长江北岸刚下过河船时,突然听到一阵嘈杂而凄惨的呼救声,我回头向南岸大石堆大浪看去,却原是我幺叔替张老板驾的缆载船,由于老板贪心多装了烧煤超载被浪沉了,霎时乘客和船板及杂物,如树叶飘浮在江面半沉半浮时隐时现而传来的呼救声。”说也奇怪,想不到江水有如此之威力,船翻了把煤倾泻后,眨眼工夫,船就被撕扯成碎片,所有碎木板,像草船借箭一样,射击落水者。我幺叔游泳可算冠军,既有体力也有经验,他见快要沉船了,就弃船而逃,而且很快离开了人群。我正在为他庆幸时,不料从水底下冲出一块撕破的木板向他射去。也许因此受了伤而沉下水后,再也没有浮出水面。从此我才知道,会水并不能保证安全,就怕受伤和受刺激神经僵硬后无力自拔……”
这是《死了没埋的人》中的主人公叙说的一个故事,田洪光说,这是老船工讲的真事,不是虚构的。
1960年,田洪光产生了将老船工的故事记下来的打算。有一段时间,他独自生活在一条25吨的驳船上,从涪陵、武隆、彭水、秀山沿长江顺流而下,运送一些衬衫、鞋帽之类的生活用品。有时,船停靠在小码头,一天“不装不卸”,他就点起铁铜色的马灯,在船尾的铺上弓起膝头写作,记录下茶馆里上百个老船工的故事。
一次靠岸时,他的小驳船与轮船相撞,“轰的一声”,驳船尾巴被撞出了一个大洞,“丢了扫把、衣服、布票、叶子烟、半斤盐巴、半斤菜油和几斤米”。
他辛辛苦苦记录的那些资料,也顷刻间顺着江水漂走了。写作的事情暂时被搁到了一边。
120万字手稿
1982年,这个摸透了川江秉性的老船夫终于退休了。田洪光喜欢给孩子们讲川江上的故事。有次,大女儿田家随口说过一句:“要是能写下来就好了。”没想到,田洪光真的听进去了这句话,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

重新拾笔的田洪光每天坐在书桌前,从早写到晚,最多的时候,能写上12个小时。那时,没人看重书桌上这摞越来越高的稿纸。对于5个子女来说,这充其量不过是父亲“消遣晚年的最好办法”。
可谁曾想,在早春一个毫不起眼的日子里,这个像蚂蚁一样勤力写作,只有小学文化的老人,终于在手稿上重重地写道:“1992年2月初稿完毕,谢天谢地!”
田洪光的手稿被大女儿田家用塑料口袋小心地包裹着,放在柜子中。薄薄的稿纸有些发黄变脆,轻轻一碰就可能裂开,蓝色的圆珠笔字迹也已经开始褪色。一展开时,一股发霉的味道就冲出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田洪光兴冲冲地将一大捆用圆珠笔写下、共120万字的稿纸抱到一家杂志社投稿。编辑叫他等等,不过从此再无音信。两年后,焦急的田洪光致电杂志社,竟被告知稿件已经不知所踪。万幸的是,当初写稿时他用了复写纸,还留下一份底稿。
田洪光终于意识到这本“手写的历史”是多么脆弱。后来,在四儿子田太权的劝说下,已经70多岁的老人决定学习五笔字形输入法。
田洪光的电脑桌旁,放着的一本自制的五笔生难字速查本,他不会拼音,就只能打五笔。有很多生难字不好拆,他就按1957年在文化宫学的四川清音韵脚诗“二月桃花落水面,楼台倒映弄池堂”,把生难字按音韵分别排列在里面,120万字的手稿,他就是这样边查边输入到了电脑上。这本将近有10年历史的小薄册子快被翻烂了,就连生锈的书钉都露在了外面。

2004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又差点毁了田洪光的写作之路。
一次体检,田洪光老人被检查出患了食道癌。手术后,他的体重从120斤直掉到80来斤。可即使是在医院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田洪光就吵着要出院,他想回家修改自己的小说。儿女没办法,只好把他的稿子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带进病房,让他在病房里继续写作。
好事多磨,老天爷还故意开了个玩笑,一场手术加上年事已高,田洪光全部忘记了原本记住的五笔电脑输入法。但性格倔强的他却不服输,又开始学习电脑,重新背枯燥的五笔字根。
随着年龄的增长,田洪光的记性越来越不行了,有时候想输入一个字,却发现打不出来,他只能去查字典搞懂偏旁部首,可是第二天又忘记了,一切就又要重新开始。有时气极,他便会在家里“拍桌子、打巴掌”。可这一切都没能让他放弃自己的写书计划。
10年,田洪光用他不大灵活的手指,将手写的小说全部敲进了电脑里。
今年1月8日,由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和重庆先锋电影制片厂联合主办的电影展映季上,田洪光的小说《死了没埋的人》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获得优秀剧本奖。
一部纪实文学
翻开印着“乌泱泱的拉纤队伍”的封面,里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细小的文字,对于年轻人而言,这部小说很难有兴趣往下读。但其实,这部小说讲的确是当下以及未来的年轻人再也看不到的长江。
田洪光说,“弄船”这个行业,就是在“血盆”里抓饭吃。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那时川江的凶险。作为长江上游河段,这段从四川省宜宾市到湖北省宜昌市的重要航道,长1000多公里,几乎每5公里就会遇到一处“要命的险滩”。

书中,桡夫是最底层的普通人,一条船上,只有“驾长”钱多一点,桡夫只能混口饭吃。他们天天穿着湿漉漉的裤子在沿江沟壑中卖力,被人视为“二流子”,还常常被码头上的土匪、权贵打骂,还随时可能丧命。这就是那群“死了没埋的人”。
现实中亦是如此。田洪光记得,他当桡夫时,船老板姓周。每次上船之前,老板都要对船工大声发表声明:“先说明了,不使力的,拉到岸上去饿莽莽(饿饭),死了不要怪我!”这时,体质不好的年轻人就会在心里打哆嗦。他们一旦被发现偷懒,就会被老板在半途中扔到岸边,要么被野兽吃掉,要么饿死。
“背砂锅”是田洪光最痛苦的记忆。从重庆到宜昌是下水,从宜昌回重庆叫上水。下水满载货物,需要很多桡夫,而上水已经没有货物,老板就要开人。被开走的船工,只能背着粮食和砂锅自行解决返程的伙食问题。而在那些险峻的荒郊野岭,船工们谁也不会等谁。如果掉队,便会面临死亡的威胁。
这就是那时的船工所要经历的一切,生于岸上,死在江中。每每说起这些,田洪光就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如今,川江上没有了桡夫,没有了急流险滩,有关长江往事的记忆变得越来越珍贵。83岁时,田洪光开始写第二部小说,故事讲的是解放后的船工。8年,小说离完结还有一大段距离,记性也越来越不好使,田洪光焦虑万分。他说:“等我们这辈人死了,还有哪个来讲川江的故事?”
“回去的路太远,太难,小脚板,走不快,怕遭丢下,怕野兽,怕生病,怕饿倒,死在路上,成为孤魂野鬼回不了重庆……”
田洪光的川江号子的声音在屋内回荡着;川江上,再没有号子声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