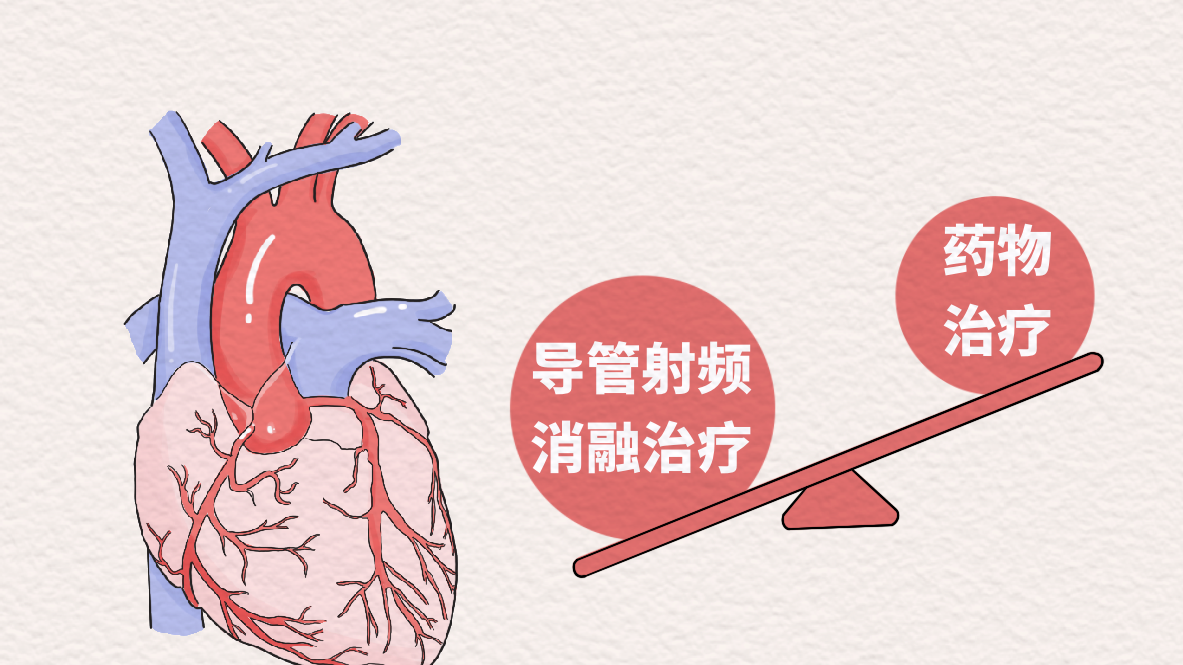四分半|温存救助站 无舟也渡人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记者 姜念月 文/图 黄宇/主持
汽车在建新西路宽阔的主干道上突然减速,拐进了喵儿石社区某个岔路口。若非提前做了功课,第一次来肯定会迷路。
沿着这条不起眼的小路往里,目之所及,是大树底下伸着懒腰的猫、屋檐下摇扇乘凉的老人,三三两两玩游戏的孩童,都氤氲着生活的烟火气。让人感到踏实与真切。
再往里,有一清静院落——重庆市救助管理站(下称“救助站”),社工杨小艺已在此工作了9年多。
一条小路,两个世界。那头是繁华都市,忙碌男女;这头是幽静庭院,闲适居客。但事实上,任凭生活如何忙碌,“那头”的路人终有家可归,“这头”的居客却仍在漂泊。
杨小艺说,救助站就像是一条摆渡船,载着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要过一条名为“流浪”的河,为那些走投无路的人生找到新的去路。

孩子们正在救助站里打篮球。重庆市救助管理站 供图
问路
下午17点,老刘略微发福的身影出现在救助站门前的小路上,只见他步态闲适缓慢,两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被他硬生走了5分钟。
“我回来了,本子拿来我登记嘛。”老刘站定门岗前,把左手的棋盘夹在腋窝下后,接过门岗递来的登记册,打开签字笔盖,龙飞凤舞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罢后又端详了一下,然后抬高了音调问:“怎么样,字还好看吧?”
老刘的字确实好看,好看得让刚入职时的杨小艺很诧异,写着这么一手好字的人怎么会住进救助站。后来,她才知道,老刘到这里来,是因为他“迷路”了。
“他说自己是‘问路’的人。”杨小艺说,老刘今年50多岁了,在他年少时双亲过世,目前又孤身一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以,在历经半生漂泊后,他自己找到了救助站。
那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夏日,他穿着脏兮兮的背心,登了一双破烂的拖鞋,提着一个装着象棋的塑料袋,像一只“落汤鸡”似的站在了救助站门岗前。

救助站里的手工课一直以来都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重庆市救助管理站 供图
“我找不到路回家了,来问个路。”这是他对匆忙跑来的社工说的第一句话。杨小艺说,那时老刘像是在哭,但由于后来的日子,刘老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所以她也有些不确定老刘是否真的为“走投无路”而哭过。
但老刘却坚决否定了这种说法:“生活嘛,总有起起伏伏,没什么好哭好怨的。”老刘说,在最风光的那段日子里,他游览过全国各地,看尽了所有自己想看的风景。至于怎么来的救助站,老刘说想不起来了。
老刘不是失忆,他只是迷失了。几番追问下,他才用极低的声音嚅嗫:“有朝一日,等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就不会住在救助站了。”那时,老刘嘴角的笑意消失了,他的低语里透出一种坚毅。
“有的人来救助站是身理出现了问题,而有的人是在自己心里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来。”杨小艺说,像老刘一样的求助者并不少,他们唯一能解决的方式,就是为自己的逃避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毕竟他们觉得,身无分文后到救助站来其实是挺伤自尊的一件事。

求助站的社工正在和受助人员进行交流。 重庆市救助管理站 供图
翌日,又是一个大晴天,早上9点,吃过饭的老刘提着他的棋盘再次离开了救助站,观音桥、解放碑、杨家坪和沙坪坝等商圈都是他可能要去的地方,摆上一盘棋,聚集一群人,“战”一下午。
运气好,他便用赢来的钱买盒市面上最便宜的烟,输了,他便早早地回救助站和遇见的所有人聊天。有时,碰到他口中“怨天怨地”的人,老刘还会去开导一番。
这就是老刘,他坚持用“只是来问路”解释着救助站里的生活,用“暂居处”诠释着这个栖身之所。从此,在救助站大大小小的活动上,都能看见他龙飞凤舞的书法和略微发福的身影。他和站里的每个熟人聊天,送走每个可能再也不见的朋友。殊不知,这“暂居处”已于默然间变成了载着他渡河的那条船。
杨小艺说,她不知道载着老刘的船何时能靠岸,也不知道老刘究竟要问哪条路,但无论河水如何汹涌,在靠岸之前,这船,永不倾覆。
寻子
在你的概念里,救助站里的“住客”都是些什么人?
一开始,杨小艺也认为,救助站里的人都不正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却发现自己错了,哪怕这些受助者们失去了亲人、家庭甚至记忆,他们也只是一群被迫“流浪”的普通人。
“我是苏州人,我要找儿子,我想回家。”
白发苍苍的老人笔直地端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他在说这句话时目光投向远方,没有焦点。他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年龄,也不记得家人的名字。每天,他都会坐在宿舍的窗前安静地看着远方,一旦有人试图与他交谈,“苏州人”和“找儿子”就是他唯一能传达的信息。
“他是被派出所送来的。”杨小艺说,受助者们被送到救助站后,社工、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等都会积极介入,通过沟通获得受助者的个人信息,再与其户籍地的相关政府部门联系,最终将他们送回家。
但起初对于这位无名氏老人,他们却束手无策,因为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好在,老人识字。

在特教老师的指导下,未保中心的孩子正在学习弹琴。重庆市救助管理站 供图
通过记忆再认的方法,老人从地图上找到了最熟悉的辖区。通过与当地街道的确认以及多部门的跨省协作,老人的身份被确认了,他姓王,今年72岁。
“故乡无亲人,婚姻已破裂,儿子在国外,这就是他的处境。”在杨小艺看来,类似王老这样的受助者并不少见,但每每遇到后,总也难免跟着难过一场。
但越是难过,越要坚强。如果自己没有强大的心,又如何撑得起别人的天?这也是为何,许多救助站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总像是一副“铁石心肠”。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王老被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护送着踏上了回家的路。离开前,他紧紧握住了社工的手,一双原本无神的眼睛渐渐泛起泪光。杨小艺说,虽然王老已没了亲人,儿子也没能联系上,但由于寻人时的摸排询查,王老在家乡的许多老朋友和老同学都已知晓了他的处境,自发组织起来接他回家。
“无论如何,这个险些‘忘了自己’的老人,他总算是回家了。”杨小艺说着,合上了王老的档案,但她知道,这不会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受助人被送进救助站后,社工第一时间赶到沟通。重庆市救助管理站 供图
出走
魏雯婷在救助站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下称“未保中心”)工作8年了,职业是特教老师,与杨小艺不同,她每天要面对的都是一些未成年的孩子,王波就是其中之一。
“我叫王波,3岁走失后被拐卖到四川。我捡过垃圾,在工地上搅过沙子,我是趁人不注意时跑出来的,然后流浪到重庆。我不知道家人信息和地址。”坐在魏雯婷面前的王波是在观音桥天星广场流浪时被民警发现的,比起其他小孩,他的表达能力明显流畅许多。
王波在救助站时话不多,便是同寝室的孩子也很少能和他说上一句话,每当有工作人员与他谈心时,他总是低下头一言不发。但是,每天早课过后,王波总是往图书馆跑,在书架前“遛”一圈手中就多出几本书,一坐就是一整天,仿佛只要有一本书,这个男孩在哪里都能过一天。
不仅如此,王波的到来俨然成了未保中心的“学霸”。除了能在老师的辅导下阅读名著、朗诵英语、解答数学、了解国学、学习画画和弹琴唱歌外,他还能很好地完成各式各样的体育项目和行为礼仪技能,在每周读书分享会上也能侃侃而谈。
一个从小被拐卖,没有受过教育的13岁孩子如何能做到这些?魏雯婷疑惑了,但王波却回答她:“我是自学的。”
显然,王波的解释并不能说服魏雯婷,不久后,由公安机关送来的王波的DNA检测比对报告也证实了魏雯婷的猜测:所有身世包括名字都是孩子自己杜撰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正在“满世界”找他的父母。
此时,距离王波离家已经3个月了。
DNA检测比对报告出来后的次日下午,王波的父亲、母亲、姐姐、表姐和外公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救助站未保中心门口。当远远地看见从中心里走出来的王波后,五人再也忍不住地大哭出声,尤其是王波的母亲,扑上去抱住儿子后哭倒在地。
“儿啊,儿啊,你到哪里去了?”
母亲声嘶力竭的呼唤在救助站里并不少见,但王波接下来的话却让魏雯婷措手不及,他说:“魏老师,我不认识他们。”
然而那一刻,王波也是泪流满面。

特教老师正在给未保中心的孩子们上语文课。重庆市救助管理站 供图
行为和语言出现矛盾的情况魏雯婷不是没见过,但当这种情况出现在一位健康的孩子身上时,她百思不得其解。
社工从心理方面介入了解后才发现,王波之所以选择离家出走并拒绝和家人相认,是因为上课时间玩手机被老师发现没收,他害怕父母责骂和同学的嘲笑,遂开始了3个月的“自我流浪”。
好在王波最终回心转意,和亲人一起回家了。然而,救助站并非只有一个“王波”。
近年来,孩子出走后被送进救助站的情况开始凸现,他们有着非常相似的原生家庭:父母不善沟通和严格要求,只在乎孩子学习好坏而缺乏心理关爱。所以,这批常人眼中的“好孩子”选择了自我放逐,他们否认亲人、否认从前甚至否认自己。
每当这时,救助站里,一个又一个“魏雯婷”开始扮演这些孩子的临时父母、临时老师和临时朋友,通过观察与疏导,选择正确的方式去打开他们已经关闭的心扉,包括对他们的父母进行教育指导,让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找回“出走”的生活。
流浪可以没有缘由,但没有出走毫无起因。魏雯婷说,纵使8年来有千百次想要放弃的念头,但一想到那些徘徊在生命的来处,还未“渡河”的孩子们,她就放不开手中撑船的杆。
回家
据重庆市民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临时救助12220人次。重庆市救助管理站救助4294人次。
这些,都是“渡河”的寻家人。
“明天我们就会安排把你的爸爸送回家。”下午18时,杨小艺打完了当天最后一个沟通电话。次日,她将会衔接相关部门安排一位鲁姓老人搭上回老家的长途汽车,他有20年没见女儿了。
为了说服鲁老的女儿配合救助站将父亲接回家,杨小艺已经给她做了4天的工作,毕竟这位老人离开时,他的女儿年仅1岁,父亲20年的缺位是她内心无人知晓的伤疤。
但如今,被送到救助站的鲁老60岁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而这就成了杨小艺下定决心要完成的任务,不管说服他的女儿有多难。好在,杨小艺成功了。
下班后,杨小艺带上耳机,点开音乐,走下办公大楼,走出救助站,穿过来时的蜿蜒小路,一脚踏进车水马龙的主干道。
忽然,她回头看了看身后走过的路,然后说:“我们说救助站的求助人是在‘过河’,但对他们自己来讲,来到这里其实是为了回家。”顿了顿,她又忽然展颜笑开,“我也要回家了。”
“彼岸烟波流转,可有人寻我。对岸繁华三千,可有人渡我。”渡一条名为“流浪”的河,寻一个叫做“温暖”的家。
(除工作人员外,受助人均为化名)
841ffd0e-2923-46f1-85ff-f147203e943d.jpg)

 无障碍
无障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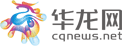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