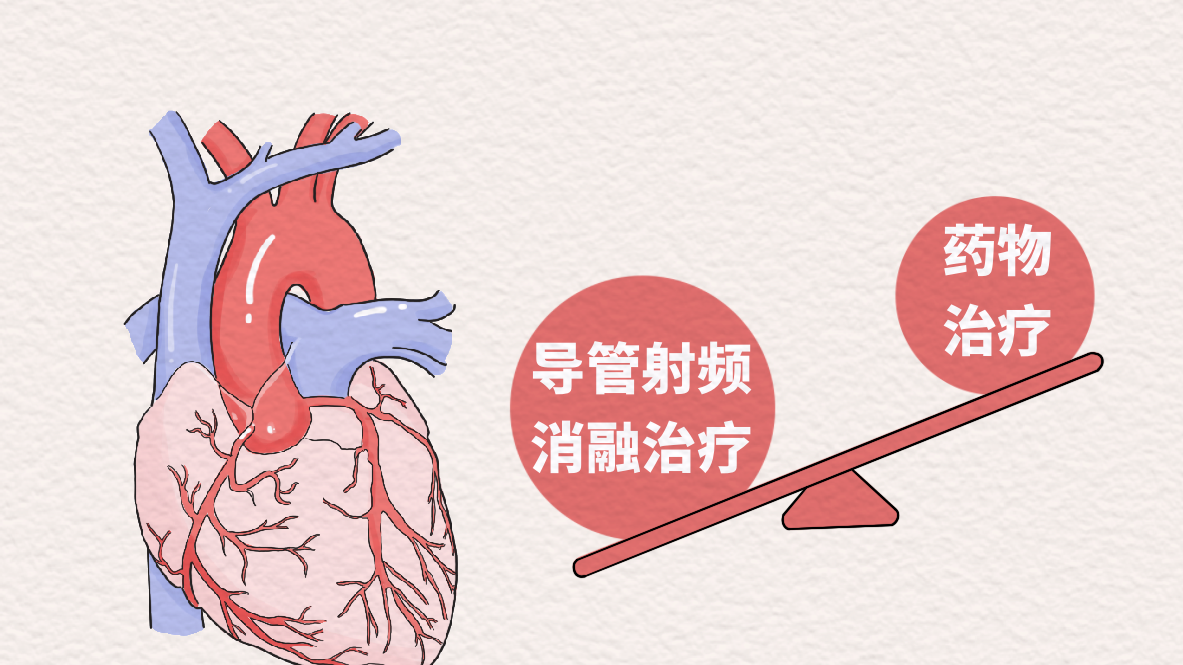寻访红色印记|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 重庆地下党学运小组书记廖伯康讲述重庆学运往事

廖伯康接受采访。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人物档案
廖伯康,1924年11月生于重庆,1945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任重庆地下党学运小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青年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1983年调回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1988年调四川省政协工作,担任第六届省政协主席。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一百年前,革命先驱李大钊在《青春》中的豪迈语句,激励着成千上万热血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
重庆解放,镌刻着无数革命青年的青春印记。1950年1月23日到29日,在宣告重庆转入正常管理阶段的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55名青年团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是400名与会人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廖伯康作为青年团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
1924年11月生于重庆的廖伯康,1945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解放前曾任重庆地下党学运小组书记。
6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赶赴成都,见到了已97岁高龄的廖老。
廖老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面对家乡来客,老人一开口便高兴地说:“我是重庆人,今年97岁,重庆住了56年,南京、上海、北京、莫斯科各一年,成都住了37年。解放的时候,我在重庆。”
循着久远的记忆,在廖老两个多小时缓缓的讲述中,我们看到重庆解放前那段至暗岁月里,革命青年们的坚守和激情;看到解放后青年共产党员们的朝气蓬勃、至善至上。
历史虽已远去,但从未被遗忘。
至暗时刻的坚守
故事从1948年5月说起,那是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至暗时刻。彼时,24岁的廖伯康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按上级安排,准备前往台湾。
“1948年5月,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特务带上叛徒,企图抓捕上海局的同志,上海地下党组织处于戒备状态。”廖老回忆说,当时上级组织规定,对重庆来的人,要特别提高警惕。
就在这个时候,廖伯康的初中同学周正平到上海找他。周正平是重庆地下党的一员,是廖伯康的初中同学,也是他另一位中学同学胡甫臣的入党介绍人。
廖伯康初中就读于巴县中学,高中上的重庆联中,即现在的重庆七中。彼时的重庆联中是一所进步学校。
“我参加党的进步活动,是从重庆联中开始的。”廖老回忆,受胡甫臣的影响,自己和包括胡在内的班上三位地下党员、两位积极分子一道,组成了地下秘密学习小组,一起学习进步刊物。
周正平正是到南京找了胡甫臣之后,胡让其到上海找廖伯康的。
“我告诉他,我没有组织关系,介于同学关系,先帮他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我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我的上级。”廖老对这一段记忆犹新,“上海地下党的一位领导得知情况后,认为可从周正平那里了解更多重庆地下党情况,于是让我代表党组织和周正平谈话,让他把所知道的关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无一遗漏地向组织报告。”
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前,周正平是重庆地下市委机关特支书记。当时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妻子正在医院生小孩,委托周正平照顾。“周告诉我,当时刘国定好些天没有来看他妻子和孩子,这时身边不断有人被捕,病房外出现行迹可疑的人,周判断有人叛变,赶紧离开重庆到南京找上级组织。”
廖老回忆,这次谈话非常郑重,每一句话都力求准确,符合实际。谈话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之后廖又将周的情况向附近等候的上级领导朱立人汇报。“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周正平没有叛变,是跑出来的。第一,那位叛变的书记如果把周暴露了,谁照顾他妻子和小孩。第二,重庆地下市委的经费由周保管,如被暴露肯定会被特务拿走。而且周在南京待了十几天,南京同志平安无事。所以我们认为周正平是可靠的。”
之后,廖伯康为周在华山医院的药房找了份工作安置下来,要他断绝与外面的一切联系,以免被特务、叛徒跟踪。
不久,党组织决定派人去重庆支援。“因为我与重庆地下党没有组织关系,并且知道重庆地下党被破坏的经过,在重庆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工作条件,是合适的人选,组织决定改变派我去台湾的安排。”彼时的廖伯康已做好准备,虽然重庆到处都是特务,极为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危机四伏的逆行
1948年9月,临危受命的廖伯康带上他所联系的上海、江苏、浙江的10位青年同志回到重庆,开展地下工作。
廖老说,当时派他回重庆,除了他对重庆很熟悉外,还和重庆一个进步社团青民社有关。这个社团由当时民主人士胡子昂的儿子胡克林创建,一起回重庆的10位同志,就是借助这个社团及其社会关系作掩护。
离开上海前,上级组织给廖伯康交待:重庆情况很复杂很危险,务必谨慎从事,独立开展工作。继续由上海党组织领导,不能同重庆地下党建立联系。和他一起回重庆的地下党员,不能发展党员,以免产生组织错乱。
在此情况下,廖伯康是如何在重庆开展工作的呢?从廖老的回忆中,我们得知一段“巧遇”。
通过胡克林的关系,廖伯康一开始就在青民社的“友恒商行”工作,对外身份是副经理。1948年10月下旬,地下党员、“民建中学”副校长潘其江找到廖伯康,问其“通过什么关系从上海回来的?”廖含糊其辞未予回答。
一周后,潘其江再次找到廖伯康,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你是党员,就和我们建立组织关系;如果你不是党员,我们就发展你入党;如果你两者都不同意,我们建议你到其他地方去开展工作,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潘其江第三次找到廖伯康时,廖的态度变了。因为在此之前,廖伯康收到来自上海地下党组织寄来的信。按照约定,上海方面每个月给廖一封信,这是第二封。
“信的内容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廖老一字一句背出信的内容,“此间南货生意发生亏损,渝地业务以就地经营为宜。”廖伯康说,这封信说得很明确,上海出事了,重庆活动以和当地联系为宜。“所以我决定和重庆建立关系,同意与其领导见面,潘约好接头暗号,地点就在我住的地方。”
当时与廖伯康同屋住的另一位副经理叫刘兆丰。在约好和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人接头那天,廖伯康暗示刘兆丰行个方便,暂时离开。但到中午11点多,刘兆丰还没有走的意思。
“见面时间快到了,我有点急了,直接说‘兆丰,我有位老朋友多年没有见面,有很多话要说,你在不方便,是不是请你今天让一下位。’没想到刘兆丰直接说,‘你这个老朋友是不是叫这个名字’。我一听,正是约的暗号,便回了暗号。原来刘兆丰就是和我对接的地下党领导。”廖老说,随后,党组织指派他担任沙磁区、南岸区的特支书记,并筹建市中区特支。
白色恐怖下的斗争
1948年春夏,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仍有一些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白色恐怖中,在没有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仍然继续进行斗争,独立应对变局。此后,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重庆地下党对各校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调整,到1948年底逐步恢复联系。上海局同时从北平、成都、上海调集力量,通过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协”“新青”,重新把进步青年和学生团结组织在党的周围。
“这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是抓不完也杀不绝的。重庆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又威武雄壮地走上反美反蒋斗争的舞台。”廖老说。
1949年轰轰烈烈的“四·二一”反内战、反独裁、争温饱、争生存、要民主、要自由等一系列学生运动,就是川东和川康两个系统的党组织直接领导的。
南京“四一惨案”发生后,重庆广大学生义愤填膺。4月15日,全市有42所学校的进步学生成立“重庆市学生争生存联合会”,号召学生总罢课,并决定在4月21日举行全市学生示威请愿大游行。当时报名参加游行的学校有57所,占全市大中学校总数的2/3以上。游行准备期间,各校广泛开展各种校内和校际间活动,全市学校一片沸腾,反动当局惊恐万分,准备实行大逮捕。
重庆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情报后,为避免无谓牺牲,4月19日晚上决定,把集中的全市大游行改为分区或校内游行集会。党的决定迅速传达到学联总部和各区、校联络点,最终说服学生们改变游行方式。
21日这天,各校学生在敌人重重包围封锁下,在各区或校内举行游行集会。沙磁区游行队伍包括前一天从北碚、青木关来的学生达7000人,南岸海棠溪地区的游行队伍也有3000多人。江北盘溪地区民建、蜀都中学等校,也集中了几百人沿着嘉陵江岸游行,与重大等校的游行队伍隔江相望,互喊啦啦词,互相鼓励声援。其他学校大都在校内集会游行,发表演说、演出话剧等。全市性大游行虽被迫取消,但在敌人重重围困中举行的游行集会,气氛更为悲壮。由于及时改变斗争策略,既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又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运动获得全胜。
“那时我们的啦啦词有‘国民党,王歘歘,看到看到就要垮’之类,朗朗上口,在同学中广为流传。”廖老回忆。
“四·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学生最后一次大规模运动,从校内发展到社会,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是一次很成功的学生运动,通过运动的斗争实践教育团结了广大学生,为迎接解放做好了思想准备。
廖老清楚地记得,各校复课后,地下党和地下社通过各种形式,在各校内进一步开展社团活动,培养积极分子,深入扎实做了许多团结教育学生的工作。10月以后,又发动“应变护校”斗争,保护学校校舍校产的完整,避免破坏损失。1949年11月30日凌晨,社会大学的学生在“抗战胜利纪功碑”(即现在的解放碑)上升起了第一面迎接解放的红旗,留下了解放前重庆学生运动最后一幅生动壮丽的画面。
百废待兴中的奋斗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
按照各大城市解放时的惯例,地下党领导的学运系统划归青年团领导。为此,廖伯康于1949年12月9日到重庆市青年团报到。同时,重庆地下党领导的学运系统成员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青年团工作。
百废待兴之时,团市工委主要抓了十件大事: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成立市学联筹委会;组织地下党外围组织会师;参与组织庆祝重庆解放大游行;组织万人禁用银元宣传和游行;协助公安部门在学校内清理敌特;参与组织杨虎城将军暨渣滓洞白公馆中美合作所死难烈士追悼会;选举参加市各代会的学生代表;举办寒假青年干部训练班;在《新华日报》上开辟“青年干部”专栏。
“那时,团市工委除少数干部留在机关工作外,绝大部分都背着背包走路下基层,回来开会既没有宿舍、招待所可住,也没有会议室可坐,只能打地铺。”廖老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团市工委专门制作了几十根很厚实的木板凳,每条两尺宽,一丈多长,放在小礼堂内,既可坐着开会,晚上也可作临时床铺睡觉。
令廖老难以忘怀的,还有同事们亲密无间的关系。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十分融洽。大家都不称官衔,除康乃尔年岁较大,大家尊称康公或康同志外,其他都直呼止舟同志、德林同志,或亲切地喊老李、老曾,没有称李书记、曾书记的。
生活上大家更是打成一片。回忆往昔,廖老仍感到格外温馨。他说:“那时青年团西南工委重点抓团重庆市工委,特别是重庆的学生工作。我常到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康乃尔处汇报工作,有时夜太深了,就挤在他办公室的小床上和他抵足而眠。”
廖老回忆,市第一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建设人民的新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出席了开幕式。刘伯承作了《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时任重庆市市长陈锡联向大会作了《关于重庆接管工作》的报告。大会闭幕的前一天,邓小平向大会作了《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传出的指令明了、政策清晰,会后大家都很高兴,参会代表相互致意。”回忆起七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廖老尤为怀念当年并肩战斗的同志们,他们表现出来的旺盛斗志,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勤奋好学的优良品德和工作作风,至今令人动容。
后记>>>
不忘初心 永远前行
采访接近尾声,当记者问廖老对建党100周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时,廖老脱口而出:“100年了,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前行!”
廖老至今记得74年前入党时的场景。那是1947年7月,他的上级黄可把他约到黄在南京学生公寓的宿舍,并为他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由于没有党旗,我们就临时画了一张党旗贴在墙上,然后他带领我举起右手对着党旗庄严宣誓。”
“对共产党员来说,为国为民是没有止境的。”廖老语气缓慢,却十分坚定,“入党宣誓就是承诺,因此我的初心一直不变,永远不变,永远前行。我们的前辈这样,我这样,我希望后辈也一如既往。”廖老特别寄语当代青年党员,一定要有真本事,把本职工作做好。
虽年事已高,廖老仍坚持学习,关注时事,尤其关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他说,成都和重庆如何在成渝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发挥各自优势,实现1+1>2的效果,这是唱好“双城记”的关键,也是两地青年党员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
重庆日报记者 戴娟 颜若雯

 无障碍
无障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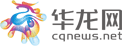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
亲爱的用户,“重庆”客户端现已正式改版升级为“新重庆”客户端。为不影响后续使用,请扫描上方二维码,及时下载新版本。更优质的内容,更便捷的体验,我们在“新重庆”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