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巫溪陡崖森林 长在人的肩背上
▲被落石砸伤的指甲
▲15元一双的胶鞋最好的地方就是,哪怕很扭曲地站着种树,它依然不打滑。
熬盐产生的盐碱灰飘到空中落在后山的石头上,遇到雨水就会形成一层盐碱结晶,多年的熬盐使这层结晶越来越厚,山上也更难长出东西。
▲贺言修说哪怕就手这么大一坨土,到了后来都很难看到了。
想种树,得先手脚并用地背树上山。
▲去年种下的刺槐已经开始抽芽
▲开饭前,工友们相互逗趣儿。
▲工人们的饭碗都统一挂在外面,但是从来不会搞错。
▲种树人的下面是几十米深的水库,左右是绝壁,绳子是最后的保障。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守护青山绿水,建设生态文明,这12个字的分量,放在大地上,就是千千万万的双腿和双手跋涉与创造的分量。
巫溪县是石漠化改造的典型样本,都是陡坡山地,泥土和水全靠人的后背和肩膀背上山。我们将带读者一起见证造林重建的艰难——这份艰难,会是一代人、几代人的艰难。人欠大自然的债,终究要人来还。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难,这一代人需要更多肩膀来担当。
巫溪县宁厂镇,7里半边街。
63岁的贺言修说,从他记事开始,四周的大山就全秃了,没树,连最后几根茅草都割来烧火了。石头缝里最后一星点指甲壳那么大的泥巴,也用手抠小刀刨,挖出来,一分钱一斤,卖了。
所以山上的石头想起想起就会滚下来,砸房子,砸人。贺言修亲眼看到砸死几个人,最近的一个,就在他房门斜开外十多米。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背后的山上,43岁的官山林场副场长陈辉正带着一个50多人的施工队在攀岩造林。必须攀岩,山太陡了,要打绳子爬。山上无土,不断落石,要在石壁上挖坑,回填客土(为改良土壤从别处运来的土),栽树,每一斤泥土、每一斤水、每一斤沙、每一棵幼苗,都需要工人肩背手提,一趟一趟运上去。
他们要在石漠化的陡坡悬崖上造一片森林,也是在人的肩上、背上造一片森林。
【熬盐,也是熬人】
石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是地表植被破坏,导致土壤严重流失,基岩大面积裸露或砾石堆积的土地退化现象,74%由人为造成。
宁厂古镇的“人为”,是熬盐。
宁厂有4000多年熬盐历史,也是三峡地区古人类文明发祥地,被誉为世界的“上古盐都”。盐怎么熬?
——天然盐卤泉山上流下来,家家户户竹筒引水,进入自家灶房。灶火大锅,蒸馏熬盐。
——熬盐以木柴为燃料。山上树木尽伐。再往外,周边山上也尽伐。
——树砍光了,用煤。散煤粉,需要泥土作黏合,燃烧效果才好。于是上山挖土,山把最后一棵绿树都给了人,再把最后一抔黄土也给了人。
现在还住在这条街上,像贺言修这样的土生土长的宁厂人,也就剩下一两百。“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火的时候,街上围绕盐业生产、运输的有上万人。”他16岁开始参加熬盐工作,那时候已经是国有盐厂了。
——“种地?我记事起就没得地可种,这一片都是石头。附近山上的人也都下来给盐巴打工。”
——“燃料早就不够了,当时都是给周边县下了任务的,砍多少树,提供多少柴,挖多少土,每年运进来保证盐厂的生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最后一点泥巴,被人从石头缝缝里掏出来挖出来,手板心心上捧着,装进背篼,存满一背篼,一百斤,卖给厂里,得一块钱。山高,都是碎石,连个手可以拉住搭力的地方都没得,有人摔死摔伤。”
盐厂在1997年正式停产,因为盐业的发展、改革,燃料的死局等多种原因。
很多宁厂当地人都看到,当年刮来一阵大风,吹垮了盐厂十几米的烟囱,从此盐厂彻底停产。很多人也愿意相信那是一次天意的警告。
此后,人们陆续离开7里半边街,读书的,打工的,调走的,搬离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了,盐厂的遗址,藏在一人多高的茅草深处,锈坏的大锅里只积下雨水和露水的痕迹。
【还债难】
人欠的债,人来还。
60岁的林云喜是造林队伍里的一个工班长,断断续续跟着陈辉造林8年。宁厂这一片的石漠化改造从今年元月12日开始,分阶段进行。
这一片要在60度以上的斜坡上,挖6万多个坑,每个50厘米(深)×70厘米(直径),再石头垒好,用水泥沙浆砌牢,再用客土回填,最后种植。一个坑,要填300~500斤土,6万个坑,都要用工人的肩背去填满。
这是林云喜8年的植树经历里最困难的一段,太陡,有的地方坡度超过70度。
重庆晚报记者想跟着林云喜和陈辉上到他们作业的最高处,垂直高度300多米的地方。每上一步,脚下都哗啦啦一片响动,当地人喊的“石谷子”(碎石)窸窸窣窣往下掉。不小心踢到拳头大的石头,落下去,赶紧回头看有没有砸到人。
石头不好挖,陡坡上人又不好发力,上半身一使劲,下半身就往下滑。林云喜说:“这些不怕,怕头上落石,上面的在挖,石头飞下来,下面的脑壳上打一个包。”有人被砸伤过,万幸只是皮外伤。
施工单位买了保险,发了安全帽,一个巨型的山体上,没有办法拉满防护网,只能自己小心。
泥巴水泥怎么运?
工人用化肥袋子装,50斤一袋。水呢,用50斤的塑料桶背上去。负责供给的工人和林云喜这种班长,一天下来,要在这陡面斜坡上上下下来来回回五六十趟。
林云喜伸出脚给重庆晚报记者看他的胶鞋,15元一双,平均一周就磨穿一双,胶底和鞋面上都是洞。
这个阶段最困难的,是宁厂再往山里走,翻过一座大山的中梁水库改造工程。水库壁立几十米,有的地方就是山体滑坡造成的一个山崖断面。
25岁的陈金山前不久才加入造林队伍。他在上方一个凸起的石头上把绳子固定,然后拽住,绳子另一头缠在48岁的杨光均腰上,他一点点放下去挖坑。人就悬在崖壁上,落下去,就是几十米深的水库。
到春节前,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又一个陡面上重复这个工作,围绕水库一圈。滑坡的地表上都是砂石,要挖到60厘米或者更深,坑才能稳住,浅了或者位置不对,或者就是运气不好,挖好的坑又滑坡填了,还要返工。
宁厂山上,上到30多米,不到工人们的十分之一,重庆晚报记者放弃了:因为脚踩不到一块踏实的地面,大大小小的石头,每一块都是活的,左脚向上蹬一步,承力的右脚就会向下滑一截,人上山需要向每一块石头试探安稳,祈求安稳——这大概就是在被残酷掠夺之后,山还给人更残酷的拒绝。
【工人们】
工人们一般都在40岁以上,平均年龄要上到50岁左右。25岁的陈金山是整个植树队伍里最年轻的。
石漠化改造是个苦活,又需要大量人力。工人们都是阶段性工程临时招募的——林业局把工程计划下给各个林场,林场负责片区改造,现场指挥监督,通过工班长临时召集人力,工人按日计工资。
年轻人都去外面了,只招得到中老年。
彭正青和金良菊是夫妻,他们这样的夫妻档还有好几对。水库山壁改造,金良菊说看着都害怕,晕,她也不会游泳,“但是危险的地方嘛,都是男的去。”
中梁水库石漠化改造的现场负责人石兴明说,这些女工,除了不用去攀岩,体力和负重上不比男人差,又勤快。他吃住都跟工人们在一起,几个月不回家。
石兴明这几天正在为客土发愁。他到处打听哪里正好有工程,有大田土要处理,坑要挖完了,眼下就要回填客土了,“当年卖土容易,现在找客土难,泥巴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当年还有土可挖的时候,宁厂人是从山腰到山下,砌起两米多深的石槽,挖出的土,丢进石槽,沿着陡坡滑下来,挖得爽快。荒弃的石槽今天仍在,像是霹雳一刀,深深剖开了山的胸膛。
绿树黄土,跟人一样,都在历史的进程中,上上下下,高高低低。
【以后的样子】
陈辉负责的宁厂这一片1064亩景观生态林,工程已经进入栽植的尾声。然后就可以歇口气了?陈辉笑笑说:“哪里歇得了,栽种结束后,又要上山施肥了。根据雨水和气温,每隔20多天或者更短,要背水上山逐一浇水,然后是防虫、管护、抚育……”
石漠化改造植树,不是3月12号植树节城里人去郊外的春游。一个坑里的300多斤土,仅能支撑幼苗的童年时期。然后在漫长的时间里,需要人工抚育,以及大自然对岩石的风化,矿物随粉尘树叶落下来,混合最初这300斤泥土的养分。壮大树苗的根须,让它们钻进岩石的缝隙,适应这里的干旱和贫瘠。最终,把人掠夺的一切,一分一厘,还给山。
即使如此,石漠化改造的树林,植株会矮化。美国红枫在巫溪县城的街道上,能长到十几米高;在宁厂的山上,只能长到三五米,像营养不良的孩子。
未来是什么样子?
陈辉说,三到五年以后,宁厂古镇后溪河两岸3.5公里的沿途,栽种的金叶刺槐、三角梅、油麻藤、黄花槐、美国红枫,会在一年四季不同月份,开出不同颜色的花朵,张开不同颜色的叶片,高低错落,层层叠叠。
山不记仇,人给它一点,它还你更多。
贺言修每天看着陈辉他们背土上山造林,他说他不想搬走,他想看看未来的五颜六色。
根据巫溪县林业局今年3月发布的全县石漠化监测报告,全县岩溶土地面积395256.82公顷,其中石漠化土地面积达125004.52公顷。而整个巫溪国土面积为403,000公顷。
2017年,巫溪治理石漠化面积1268公顷。杯水车薪。
巫溪林业局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向轶波是石漠化改造的主要负责人:“一分一厘还债最难,这个治理,这种还法,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代,一代人,几代人。人为破坏一年欠的债,要多少人的肩膀十年、几十年来还……”
巫溪90%为中山地形,未来的改造,都在人的肩背上。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那些背土背水上山的人,牢牢嵌进黑黢黢的石崖的人,嵌进历史进程中的人,他们是未来长空俯瞰草木幽深中的高光点。
他们是这一代人。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刘春燕/文 李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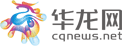
 手机阅读分享话题
手机阅读分享话题






